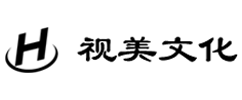会议资讯
地方戏的去处——写在2024年江苏省小剧场演出季开始之际
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地方戏的去处
——写在年江苏省小剧场演出季开始之际
王宁
中国个剧种,基本都是地方戏。其实包括昆剧和京剧,也都有很强的地方属性,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地方戏。它们与一般地方戏的区别在于,有的地方戏流播地域比较狭窄,仅限于某省的某一特定地域,它们的流播地域却较为宽阔,可以跨几个省份,甚至更广。
地方戏的这种地方属性很像植物,可以视作类植物属性。离开了“地方”,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地方戏就略显尴尬了。提到什么“世界上最美的戏曲”“世界最美的声音”,说这话的人不是偏狭,就是无知。我连你说什么唱什么都听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美?你眼里最美的,在别人眼里,可能啥也不是。就好像有人戏称某地人说话是“鸟语”,但在本地人的耳朵里,那可却是最美的声音。所以,地方戏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它的美永远只属于某些人。归根到底,地方戏的魅力正在地方,没有了地方,地方戏啥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戏就是“十五国风”,郑有郑的味道,豳有豳的趣味,并不相通。但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戏当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在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你所不知道的痴狂
地方戏是作为地方文化的血脉和精神存在的,它作为地方文化的这种属性隽永而深刻,最凸显的表征就是,它曾经激发出地方百姓持续、绵久、代代相传的痴狂。
年,我曾经到山西晋东南地区的泽、潞州(今天的晋城、长治二市)进行比较长期的戏曲文物和戏曲民俗考察。因宋代“二程”的程颢曾经在晋城做过三年县令,这里从宋金以至明清,民风淳朴、崇儒向学。明代这里有著名的北曲大家常伦,王骥德在《曲律》里面曾经提到他。清代名臣陈廷敬也是晋城人,他家的皇城相府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是这里的沁水人。但这里更为人熟知的是古建,尤其是庙宇。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好像是说,二十世纪初之前的古代庙宇建筑,山西占据了全国的四分之三,而晋东南又占据了山西的四分之三。当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就曾经长期在这里作古建考察。当时,我们考察的直观印象是村村有庙、庙庙有台。而采访老艺人和村里的文化人,则给我们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这里的人民曾经爱戏如狂。
有一个小村,名字好像叫李家庄,村里人口不多,好像只有几十口人,但只从事两种职业,要么是唱戏的,要么是为戏班做运输的。当时戏班运输主要靠骡马驮运。
记得还有一次采访,一位当地人士和我们谈起了解放前的一段往事:有一次村里唱大戏,当时的大戏都是由村里的富户譬如地主之类的人捐款赞助。而且,唱戏的时候还要打赏,就是由出资赞助的主人亲手将赏钱递给演员。这个环节很隆重,边上有司仪在大声唱名,宣称某某打赏某某演员银钱多少,所以很能提增赞助者的声望。村里有一个贫户,当时在唱戏的场合,众人就起哄打趣他,说要不你也来为村里演一场戏,当时一场戏是三天,加上打赏,花费是非常可观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个贫户竟然答应下来,为村里唱了一场戏,三天,而且打赏等程序一如既往。戏演完后,村里人才知道,就为了这一台戏,这位贫户后来用了十年,来还清这次演戏所借的外债。倾家荡产、举债十年,只为了一台戏,岂不是戏曲史上的奇谈。
其实,那个时候,在农村,戏曲和曲艺曾经是枯燥的农村生活当中极难得的调剂。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山西老家有一次去听一个来自河南的说书艺人老彭说书,说的好像是岳家将故事。那个时候村子里说书,基本是“还愿”性质,哪家生了孩子或者老人过寿之类的,都要说书庆贺。我年考上南开大学,当时在整个公社都是轰动的事情,所以母亲也订了一场书。说书之前,还要请村里和队里的干部吃饭。当时,都是在院子里说书,拉上电灯,摆一张方桌,我家有一个很好的八仙桌,所以常常被村子里借去说书用。一般都有百十号人聚集到院子里听书。常常说到晚上十一、二点。说书说到精彩的地方,满院子百十来号人鸦雀无声。我清晰地记得,坐在最前排的七十多岁的一位老奶奶,两眼含泪,一动不动。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就是这个老彭,有一次在我们村里说《白蛇传》,因为太精彩,村里人不忍故事被打断,所以,原本没有打算说书的人家也找借口说书,就为了能将故事接续下去。当时,说书艺人的酬劳是小麦,母亲告诉我,在说了一个多月之后,老彭那次离开我们村的时候,因为小麦太多,不得已专门雇了一个独轮车,满载而归。这些故事,在过去了四十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很清晰。
这些属于我身边的故事。至于江南地区,单从文献也可以看到,起码明清时期,农村百姓对于戏曲也如痴如醉。比如浙江有些地区看戏有所谓的“两头红”,指的就是从第一天的日落,演到第二天的日出,通宵都在观剧。这样的痴狂、痴迷,对于今天的年轻观众而言,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
(二)“漂泊无依”与地方戏“进城”
然而,任何对于艺术的痴迷都受到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一旦时过境迁,就可能盛况不再。以上所说的痴迷,其实是必须依托农村存在的,它的筑造者就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村民共同体。这种痴狂的存在,取决于当时特定的文化氛围、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而一旦这种共同体消散之后,那个特定的时代过去之后,曾经使得他们痴迷的民间艺术,又该归向何处呢?
中国社会当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城市化,起码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们看到大量的农民进城、大量的农村消失。老人村、甚至是无人村大量出现,在一些交通、饮水、教育、医疗条件有限的地区,已经出现大量被废弃的村落。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迁徙,使得原本的村民共同体已经解体。很多地方村子里已经没有学校,有些镇子上学校也是勉强维持。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一现象的总体得失,但它对于地方戏的影响却是直接的。在农村消散之后,有些地方戏已经处于无所归依的状态。来自农村的订单越来越少,原来演戏所依托的农村“大集”很多已经不复存在。近期,我曾经和老家临汾蒲剧团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他们闲暇时的订单,一台大戏也就元左右,最忙的时候,也不过一万多一点。几十个人的剧团,这样的收入显然是比较尴尬的。而这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很强艺术实力的剧团。
这背后的原因,因为农村和农民的解体。许多农民的后代,其实转而奔向了城市,变成了市民。原本在农村的代代相传的戏曲氛围已经消失了。进入城市后的农民,已经接受城市文化的熏染,没有了观众,没有了市场,民间戏曲也就失去了依托。
而进城曾经是中国地方戏重要的生存和提升之路。不管是从古代、近现代,还是现在,进城都曾经是中国戏曲很重要的一条提升和生存之路。宋金时期,中国戏曲刚刚发轫形成的时候,就有关于戏曲进城的记载和描述。当时一个叫杜仁杰的作家,写过一篇【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的散曲,这里的庄家就是指乡下人,我们老家今天还有一个称呼叫“庄家户”,是对农民的鄙称。勾栏是当时城市当中集中演出戏曲等伎艺的场所,当时由于刚刚兴起,所以,对于一个进城的农民,势必就充满了新奇。这篇散曲以略带调侃的口吻,描写一个乡下人因为从未见过勾栏,于是购票看戏的全过程。这个是古代的例子。近现代以江浙戏曲为例,江浙的很多剧种,其形成和成熟,很多都仰赖城市之功。比如上海就曾经对江苏的淮剧、滑稽戏、苏剧的成熟和变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越剧,如果没有在上海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今天的模样。
戏曲进城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高度商业化。比如近代上海戏园的运营,就形成了很成熟的商业模式。观众比较集中,很容易形成市场规模。城市人口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要求,对于地方戏提升艺术水平也形成了刺激。城市媒体为戏曲提供了很好的批评阵地,使得艺人可以及时得到关于表演的反馈。戏曲进入城市之后,也很容易吸引文人进入戏曲编剧和改编的队伍当中来,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士甚至可以在演出和音乐等多方面为艺人和剧团提供帮助,助力地方戏艺术水平的提升。还有,城市还可以借助独有的优势,将戏园与茶园、餐馆等融合起来,形成类似今天文旅融合的优势和便利。当然,戏曲进城之后最为重要的,是戏曲艺人在得到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可以用心致力于艺术提升,尤其是对于当红剧种和当红艺人,由于收入倍增,这种物质的刺激力度,是可以想见的。
(三)走向“小剧场”与文旅融合
当然,地方戏今天的进城多少有点无奈的意味,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一如既往,城市所具备的优势今天仍在,有些方面且有所发展,可以为地方戏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只是由于文化背景、戏剧生态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若干年内,小剧场和文旅融合,将会是地方戏进城之后非常重要也非常适宜的一条发展路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地方戏进城,其实是伴随农民进城现象采取的一种积极应对之策,其背后是舞台跟着受众走,这也是中国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规律。目前存在的大量“城一代”其实还是农民,很多农民正处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当中,很多“城一代”还保留着很深刻的农村记忆和地方戏记忆,甚至,有的还有较为深厚的地方戏情结,对于家乡的地方戏有着深切的关怀。这些,都为地方戏进城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形成了对于“体验经济”的强力刺激。戏剧体验和戏曲体验,也成为人们文化消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旅融合的一大出发点正在于文化资源在旅游市场的运用,小剧场戏曲作为应时的艺术载体,可以很好践行这一理念。它一方面可以通过舞台呈现,通过演员表演,为景点增加丰富的观赏资源。另外一方面,又通过地域性文化资源的融入,形成游历者的深度文化体验,为旅游增加全新的文化和艺术内涵。如今年举办的江苏省第四届小剧场剧目孵化入选剧目当中,就有结合苏州地域文化的昆剧《唐伯虎》,这一剧目如果能够在桃花坞“唐伯虎故居”和附近的旅游景点得以呈现,相信会给旅游者带来全新的更加深刻难忘的文化记忆。再比如清代南京的“花神”文化,至今在南京仍有大量的文化遗存,也大可以通过小剧场形式,通过小剧场戏曲予以呈现,并融入到本地旅游景点当中。
三是小剧场规模比较小,一般不超过人,相对于大剧场而言,更容易操作。现在,对于很多群众基础比较差的剧种,要想凑上千的观众,凑满一个大剧场,而且具有持续性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小剧场由于建在城市,在人口比较稠密地区,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召集观众。而如果建在旅游景点,则可以面向游客,形成分众传播。
四是小剧场投入少,参演人数比较少,降低了演出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养,形成局部市场。当代中国戏曲的一大纠结,正在于市场与行政的矛盾。具体而言,戏曲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在经费、政策等方面获得支持;另一方面,剧团又需要自谋生路,开发市场,向着自食其力的方向努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从接受政府支持角度,剧团需要接受政府领导,发出政府希望发出的声音。但从市场角度,剧团又必须围绕观众喜好,为观众贡献更多他们喜欢的戏曲。小剧场也面临这样的纠结,而文旅融合某种程度上为市场和行政的平衡兼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路径,达成市场和行政的新平衡。
五是地方戏剧种的小戏和折子戏本身与小剧场戏曲的匹配度很高。很容易通过简单改制移入小剧场。这一点,多有专门讨论,不再赘述。
综上可见,尽管带有一定的被逼性质,但正是在小剧场这一貌似逼仄的空间里,在各个旅游景点的狭小剧场当中,我们依稀看到似乎已经被逼迫到绝地的地方戏的生机和希望,甚至可以说,是新的契机和机遇。基于此,几乎可以断言,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小剧场戏曲势必成为地方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因为它可以解决中国戏曲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为地方戏的生存乃至发展寻找到新的路径。
人类其实具有植物属性,尤其是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在多数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背后,其实是离不开的泥土、忘不了的乡音、脱不开的乡情。我们总是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快乐,一如击壤鼓腹的先民。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戏正如飘在故乡上空的云,当故乡游移,它也会随迁,伴随着乡民的足迹,弦歌缭绕。
“文化地活着”才是真活着。一千多年前的中唐,白居易在他的《吾土》一诗中曾经写道:“身心安处是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宋代的苏轼也在《定风波》词中有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地方戏给我们最大的情绪价值,正在于内心的安宁。它带给我们内心的宁帖静谧,是其它很多东西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田园在,地方戏就会存在,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地方,也变换了一种方式,袅袅地唱下去。
(王宁,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戏曲研究中心主任,苏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来自【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