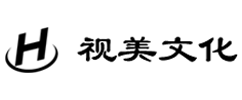会议资讯
说说戏曲演出的“叫好”与“倒好”“怼戏”
在网络用词中出现“怒怼”一词,心里总觉得这是个贬义词,主要是代表无理取闹不文明行动。可不可以用怒斥、怒批,是不是更好些,社会发展进步,语言表达却越来口语化了,比如用的“甩锅”、“忽悠”,成为全民运用的词语。
在当下网络的今天,有自媒体把许多舞台演出“事故”,称为“翻车”现场,或者戏曲演出中的失误剪辑到一起,有的现场观众当场到给演员叫“倒好”,京剧观众是用“嗵”来叫“倒好”。最难唱的天津,观众认为是不能惯着演员,认为是对演员的警示。京剧名角杨小楼、马连良、谭富英在天津都遇到叫“倒好”。许多人听过侯宝林、郭启儒的《失空斩》,因为龙套站错,演司马懿的演员刚出来,还以为观众给自己叫“倒好”。
其实舞台演出“事故”或丟词、忘词,行头失误、出错,不可避免,但是观众就是不买账,旧时剧场有扔茶壶、茶碗,乡下唱戏有扔砖头、石头、西瓜皮的,表示不满。有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时候,观众不会听台上人的解释,所以越解释越乱,愈描愈黑,会造成更激烈的行为。
戏曲中的“叫好”必须恰到好处,该“叫好”时候叫好,人们就知道他懂戏,不该“叫好”,叫了好一看就是外行,不过艺术是相同,就看你的理解如何。以前多以“叫好”为主,现在除了“叫好”,鼓掌也是喝彩的表达。京剧里面的“好”有碰头好,第一句就叫了好,还有是唱腔节奏变化自然过渡而叫好,这是唱的音好、腔好、韵好、味好。还有扮相漂亮,身段表演漂亮洒脱,称之为“有范”,武打技巧配合默契,还有高腔处理无杂音怪音,乐队伴奏高潮迭起,观众会来一句好,或者热烈的掌声,演员演唱起来也更加自信激情。
晋剧百年史话中介绍到“罚戏”,有这样的内容:旧时社首、观众对戏班和艺人的一种惩罚。戏班赶了“空台”,唱戏误了正日了都要罚戏班的戏。演员们在演出中出了事故,丢了戏,诸如:误场、笑场、上下楼梯、过河上船、武戏对打出了漏子,丢词减戏或“提洋油罐子”等都要罚你的戏。那时观众看戏是非常认真,非常挑剔的。台下合文、戏迷很多,他们很识戏,你哪一点儿少了一句唱,拉了一句词,减了一个动作,去了一段戏他全知道。甚至连上下楼梯的步数他全数着,家常规矩是上楼十二级,下楼十三级,多一级少一级全瞒不过他们,你不按规矩来,他们就给你叫倒好,没完没了地“怼”你!演完后当场兑现,社上就要罚你的戏。
罚戏班和罚演员的戏究竟罚多少,那要看具体情况:有时罚你重唱一遍,有时罚你另唱一出,象戏班赶了空台和误了会上的正日子,罚得就狠了,少者一天半天,多者也许罚你二天三天,甚至扣你的戏价。罚了戏班的戏,班主只好自认倒霉,赔钱给人家唱,罚了演员的戏,影响了戏班的声誉,班主就要和这位演员算帐了,轻者罚你的“刀头”,扣你的“份子”,重者就要请出十二家掌班,用麻绳、皮鞭和你说话了。
叫好声一两声为正常,多了就是一种“倒好”。 年,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二日,在西北俱乐部举行盛大娱乐晚会,慰劳陆空军将士。节目为《断桥》《汴梁图》《打金枝》《民主与革命》(《串龙珠》),晋剧名伶辈出,竞露意。最后一场本来是丁果仙《串龙珠》,前一场是郝翠英上的,因为没有多少台词,观众也看不出来。武蕙仙上场,照例观众在虎道门予以堂手,一开口不是丁果仙,频使观众空喜,临末丁伶始出应场,终未尽失观众所望,惜时晚戏节散乱,群情大渔懈。这场戏丁果仙在城楼上唱,最后就是观众的好声,和丁果仙唱交织在一起,表达他们对丁果仙的不满。人名气大了,自然有人要借压倒他来显出自己。徐沟王答一带是盖天红的家乡,这里的观众对于“男的不如女的,盖天红不如果子”的说法很是不满,解放前后称丁果仙为“烂果子”。太原古城营传说丁果仙刚出道在古城营唱戏,对吹打班出身的高家班说道:靠着鼓了瘪了吹打能赚几个小钱?高家班的人一怒之下从家里端来一簸箕银圆,让丁果仙三唱芦花的传说故事。传说丁果仙也是很没面子,说以后不来这里唱戏,解放后丁果仙在晋源城里演出,对此事向古城营人道歉,说那是过去的事了,新社会不用计较那些事情了。古城营刘忠林参加过太原聚文会活动,上世纪曾随丁果仙赴北京演出伴奏。太原北郊三给村也有因丁果仙演出中因为唱词问题,弄的不愉快,也是有再不来这里唱戏的气话的传说。解放后她的师父孙竹林在三给村教戏,村里的郭存喜还跟着这位二师姐演出多年,村里人一说郭存喜跟师姐丁果仙合作演出的《蝴蝶杯》和《空城计》,还有磁带录音时也是颇为自豪。阳曲县也传说因为演唱丁果仙给四个老汉下跪的传说故事。太谷、平遥都有类似的传说,都是丁果仙说:“再也不来你们这里唱戏了”。至于传说故事,大多有些影子,加上乡人添油加醋,说的神乎其神。
我也听本村村民讲过“丁果仙与十二红刘宝山在太原唱交印”的故事,这个传说故事太原人都不知道,但是故事中的劝和人任顺来却真实的存在,而且据任秀峰外甥周贵仓证实,他见过任顺来住在丁果仙家里,看来丁果仙对老艺人很尊重。任顺来是忻州名票和任秀峰同是令归村人,而且做为忻州票界前辈,刘宝山也要给这个老乡前辈面子。传说如果没有写在纸上就不好说是事实,但即使写在书里,也并非是真实事件过程,都带有双方的感情在内。
“叫好”声与鼓掌本来是为演员喝彩,有时候这种不合时宜的“叫好”与鼓掌,反而是观众不满意的表现。现在的剧场也有一种不好行为,比如剧场到时间还没有开场,观众就开始拍手,他们的意思是要快开戏。说实在,舞台各项演出步骤都是经过多次排练,但也会因为一些小的环节导致时间有所误差,其实演职人员也非常紧张。舞台监制和导演在没有把各项工作安排到位之前,确保每个细节做到万无一失,方可开始演出,台下的观众却不这么认为,觉得你们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工作。
问起太原七十多岁的戏迷,他们很少见过现场“怼戏”、“怼演员”的,但是大部分听说过。常听晋剧演员直播的时候,说起太谷水秀、胡村一带的戏,最难唱,一不小心就被台下的戏迷观众给“怼了”,有的时候“怼演员”,喊道:下去啵!让演员在台上走也不是站也不是。晋剧演员在这里演戏,心里压力山大。俗话说:“十戏九不投,对了没来由”,一出戏会有好几种不同演出版本,比如唱腔、行头、场次都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对看不顺眼的演员,也要让“回去吧”,弄的演员挺尴尬。太谷等地“怼”的演员急了,演员脱口而出“我是本乡地面的”,这样有了乡里乡亲情分,观众也就不好意思了。
在昔日戏曲的舞台上,台下总有几个懂戏文的老人,他们如鹰隼般锐利,紧盯着台上的每一个字句。演员若稍有差池,便可能遭遇罚戏加演的严厉惩罚,一人失误,全班受累,左右为难。无论是名角还是普通演员,都难逃此劫。如今,在直播快手、抖音等平台上,演员忘词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大部分乐队都能天衣无缝地伴奏,不懂剧词的观众有时也听不出来。现在有了字幕,打字幕的操作员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字幕空白或者跳过,直到演员回到原来剧词中继续跟进。
晋剧传统剧目《明公断》为例,其中秦香莲与皇姑对唱的部分,不同的演出版本有着不同的唱腔板式。名家们各有千秋,如郭兰英、牛桂英、花艳君、程玉英、王爱爱、栗桂莲等,他们的演绎各具特色。不仅是秦香莲,陈世美和包拯的唱词也有所不同。郭兰英版《明公断》是皇姑唱:我本是金枝玉叶体,怎能与庶民百姓一样。秦香莲唱:既然你是玉叶体,咱二人谁在后来谁在先。现在山西省晋剧院演出的《明公断》版本是,皇姑唱:我本是金枝玉叶体,秦香莲接唱:咱二人谁在后来谁在先。有时候演员唱习惯了两句,唱成了“我本是金枝玉叶体,咱二人谁在后来谁在先。”就把秦香莲的词也唱了。现在的演出往往不是一个团体演员组合演出,而且不同师从,唱词也各异,这就要求乐队必须对演员的唱腔、气口、转板快慢掌握得恰到好处。万一出错,就可能冷场,让观众看出破绽。但现在的专业乐队遇到演员忘词或过误场时,都会用曲牌过门补起来,直到演员正常发挥为止,观众大多看不出来。即使有观众不满意的时候,只要不影响演出,演员都会坚持演完。演员和观众之间既是鱼水关系,也是浪里行舟的过程,可能随波逐流,也可能浪打船头。
晋剧院有一次下乡演出,唱段进入滚白板式时,打梆子的演奏员把梆子放在一边,台下的观众喊到:“看外后生,早上没吃饭咋的,木头也砸不动了。”其实这是瞎起哄,因为滚白属于散板,是无板无眼,全由演员发挥控制,里面就不用梆子。
解放前太原窊流村与南寨村有太原秧歌戏班,窊流村有个艺人表演戏曲“趟马”功夫时,鼓师觉得唱个秧歌演这些多余,变换鼓板节奏催他下场。他一个圆场走到鼓师近前,用马鞭绕住了鼓师的鼓楗子,嗖的一下把鼓楗拽飞了,让鼓师来个手足无措。
说到叫好、鼓掌、还有口哨,都是观众对演出的认可鼓励,有时却是倒好起哄。以前听山西广播电台播放孙昌与阎娅祯演出晋剧《清风亭》现场录音,就有观众的鼓掌与口哨声,演出现场演出效果非常轰动。全国红梅大赛山西赛区在太原的山西省晋剧院演艺中心举行,剧场坐满了各地市专业剧团青年演员,北路梆演员郝建东和詹丽华分别演唱《血手印》中的唱段,当北路梆子乐队伴奏把演员的唱腔像冲浪一样,推动了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时,全场观众同时叫好起来,这种场面十分罕见,因为剧场叫好基本某一群人,他们大部分在一起坐的,这是四面叫好,包括山西省京剧院和参赛的各地剧团的演员也叫起来好来。北路梆子乐队演出伴奏的沈元元、侯三红、张银楼也很兴奋,同行们不仅给演员叫了,更是在乐队烘托气氛的基础上现场观众有了共鸣,所以有那全场彩声四起的场面。
村里一老人常跟别人讲,还是人家丁果仙:一出虎道门子,台下就鼓起掌来。新中国成立后晋剧名家都成为人民艺术,观众对他们是十分敬重,大部分是鼓掌表示喝彩。周瑜生孙福娥就有一声定太平之说,一个叫板都能使台下观众鼓起掌来。如今剧院里演出,名家出场也会报以热烈鼓掌和呐喊声,剧院和乡下演出不同,叫好声要点到为止,多了反而引起剧场观众的反感。